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图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事实上已经成为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论文呈几何态势增长,目不暇接,但总是感觉到非常浮泛。很多是项目体或者学位体,都是先有题目,后再论证,与传统的以论带史的研究似乎没有质的区别。在这样背景下,我常常想到经典重读的问题。
当然,如何选择经典,如何阅读经典,确实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规。中国学问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汉代称为“六艺”。《乐经》不传,古文经学家以为《乐经》实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没有《乐经》,乐包括在《诗》和《礼》之中,只有五经。唐宋之后,逐渐又有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这是儒家基本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经斋记》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如何研究经典?我的阅读范围很狭窄,比较欣赏下列四种读书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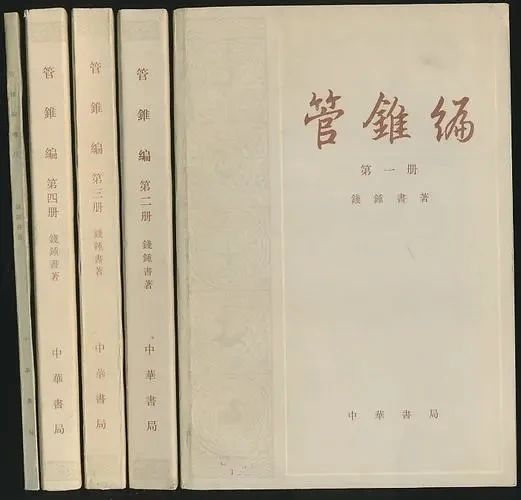
一是开卷有得式的研究,钱锺书为代表。他也是从基本典籍读起,《管锥编》论及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书,都由具体问题生发开去。在筹备“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过程中,我曾数次拜访杨绛先生。第一次去时,出乎意料,钱先生家的摆设极其简朴,且看不到丰富的藏书。据钱锺书先生自己说他读书的方法是在欧洲留学时养成的,因为当时图书馆有很多书不能外借,因此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从整理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的读书笔记来看,钱先生读书很杂,全无禁区,连字典都读得津津有味。杨绛先生说,有些书钱先生泛读,读一遍就好,而有些书是要精读的,反复去读。钱锺书做读书笔记,记下读书的每一点心得。钱先生胸中有那么多的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问题”(意识)。这是传统的读书方法。晚清俞曲园说自己“老怀索寞,宿疴时作,精力益衰,不能复事著述。而块然独处,又不能不以书籍自娱”,于是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间,做了好几本读书笔记,提出很多值得关注的课题。在他看来,从事研究,不仅仅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某种内在的强大动力。过去,我们总以为从事文史研究,姜是老的辣,其实未必如此。年轻的时候,往往气盛,往往多有创造。但是无论年轻还是年老,这种读书笔记还是应当做的。《书品》载文纪念顾颉刚先生,说他每天坚持写五千字,哪怕是抄录五千字也行。《顾颉刚读书笔记》共有十七册(包括一册索引)。钱先生也具有这种烂笔头子的功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中文之部)二十册,外文之部四十八册,多是读书笔记。这是中国最传统的读书方法,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都是这样的学术笔记,洵为一代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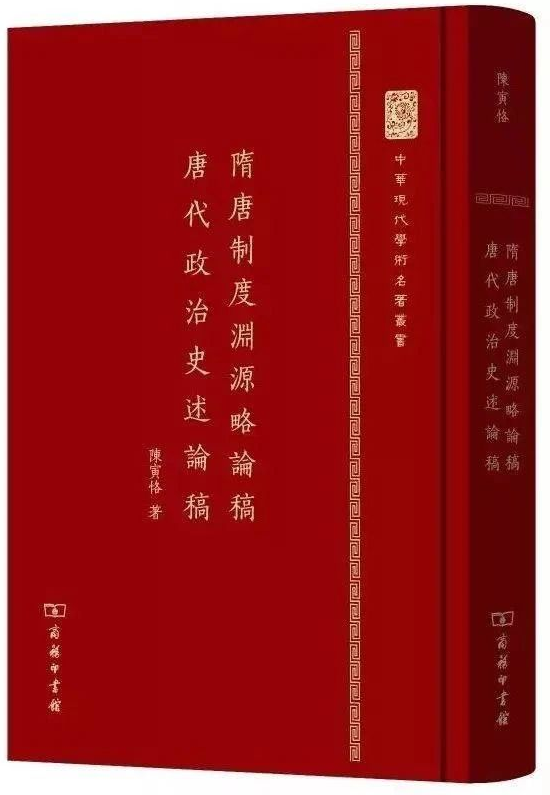
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陈寅恪为代表。问题多很具体,所得结论却有很大的辐射性,给人以启发。《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篇幅不长,结论可能多可补充甚至订正,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而充满感召力的。他的研究,有的时候带有一定的臆测性。他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说,对于古人应抱有“同情的理解”。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要有一种谦逊的心理。余英时说:“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天帝,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克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我们今天的研究,往往居高临下,急于给古人排座次,缺少一种平实对话的姿态。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指出:“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都沿用着这种读书方法,多所创获。他们的研究成果,叫人钦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关注政治制度史、社会思潮史。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其实都离不开政治制度史与社会思潮史的研究。同时,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文明也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学术要落地生根,绕不开制度文明研究。

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陈垣为代表。他的研究,首先强调对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譬如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引用资料就有二百多种。其次是研究方法,从目录学入手,特别关注年代学(《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避讳学(《史讳举例》)、校勘学(《元典章校补释例》)等,元元本本,一丝不苟。陈垣曾以上述几部重要的笔记为例,作史源学的研究,总结了若干原则:“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颠倒。六、引书不注卷数,则引据嫌浮泛。”1942年,他利用《册府元龟》及《通典》,发现《魏书》一版残叶,凡316字,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儿子陈乐素考证发现,《玉台新咏》寒山赵氏本所附陈玉父就是《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非常详尽,但是有几处小小地方,有所推测,他在给儿子的书信中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考证太迂曲。他主张一是一,二是二,拿证据说话。“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他的主要成果收录在《励耘书屋丛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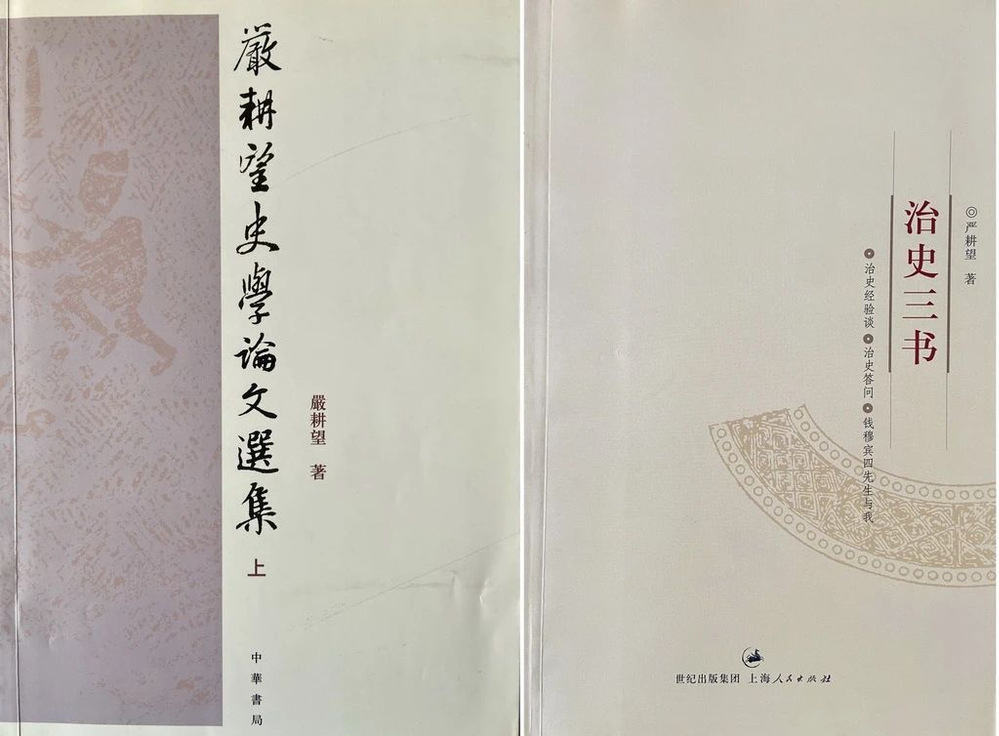
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严耕望为代表。严耕望先生的学问是有迹可循的,他也有个先入为主的研究框架,但仅仅是个框架,然后做资料长编。他的《唐代交通图考》整整做了四十年。有这样的功夫,后人再做这个课题,想超越就不容易了,最多拾遗补阙。他做《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考》,把所有能找到的佛教庙宇、高僧等,逐一编排。他做《两汉太守刺史考》,排比资料,考订异同。我发现,很多有成就的学者,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总是先编好资料长编。关键是如何编。每个课题不一样,长编的体例自然也各不相同。他的体会与经验,都浓缩在《读史三书》中,值得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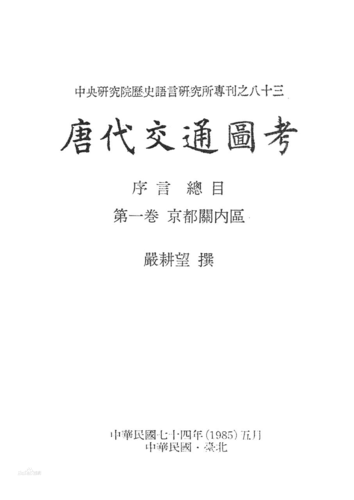
无论哪一种读书方法,我发现上述大家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选自刘跃进 《从师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