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跃进,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出版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文选旧注辑存》《从师记》等,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第四届思勉原创奖、第五届中国政府出版奖等。
摘要: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史料工作,其意义是多重的。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前辈学人开始倡导恢复、加强史料研究,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对此前二三十年的研究工作的反拔和纠偏。二、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文学研究的发展。正是由于有计划地、成系统地史料工作的推进,一些基础性的史料成果的出版,使得文学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文学方面,这个意义尤为突出。三、催生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也对整个文学史料学有重要的推动。四,整个大陆的文学研究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仰视洋人(特别是日本人),到赶超洋人,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史料工作在整体上,是有一大功的。
关键词: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史料学;文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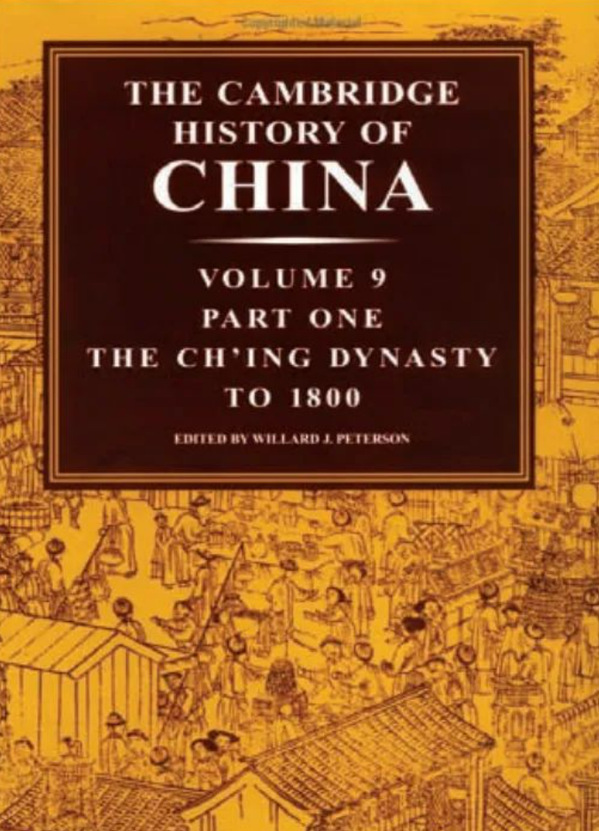
回顾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三十年来的工作,有几条基本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关于文献史料研究的价值,大家的认识逐渐趋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种理论思潮,你唱罢来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天。而今,崇拜洋人学术的时代已成过去,文化上的自信在回归。欧美汉学界业已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自己不再被崇拜,颇感失落,于是釜底抽薪,不断推出新理论。近年颇为盛行的所谓抄本时代的研究就很有趣。这种理论的成果就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几乎抹去所有大家小家的区别,理论依据就是抄本是靠不住的,只有看得见的版本才是真实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自己的研究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其结果则是消解经典。对此,我表示怀疑,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有合理的意见。一百年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所谓“唐宋分野”的话题,认为唐代和宋代确有不同。而今的抄本理论依然继续这个话题。这是因为,周秦汉唐文学主要是抄本时代的产物,而宋代以后,则进入刻本时代,文学观念、文学载体、文学形式、文学内容、文学成就都有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内藤湖南、欧美汉学,都有值得关注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对经典保持一份敬畏,保持一种尊敬。二〇二一年五月,我在《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版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史料永远不会过时”的即兴发言,特别提到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过的话。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达到的史料……”因此他说了几条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富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结论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翻史料”[1]。当然,史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史料与史识的问题,胡厚宣做过恰当的比喻:“史料就是建筑材料,史识就是建筑的构图,没有材料,再好的图纸也盖不好房子,但同时,没有图纸,再好的材料也不能成为房子。”[2]没有史料的发现,很难有学术大踏步的前进。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史料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这篇发言经过整理发表在《光明日报》,我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比较偏激的话:“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编者特别将此话提炼出来放在醒目位置。可能很多人会反对,但是我们从事史料研究的学者,大多还是认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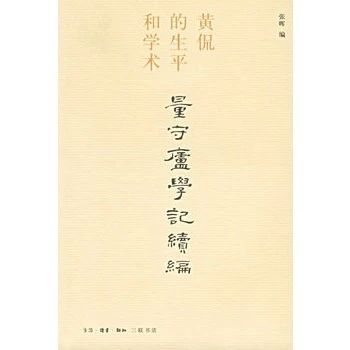
第二,关于文献史料研究的目的,大家的理解还有分歧。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有用的知识,二是有智慧的思想。文献史料研究,主要提供有用的知识。表面看,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其实这里也有高低之分。就最低要求而言,文献史料的整理,就像整理家务,干干净净,有条不紊。需要的东西,随手就可以拿到;客人来访,也会觉得赏心悦目。这样的工作,积以时日,可以做得很好。但,这不应当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张晖曾编过黄侃《量守庐学记续编》,他后记里提到很有趣的话题,即学术研究贵在发明还是贵在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主张“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就是发现新资料,推动学术的发展。黄侃主张学术研究贵在发明,就是对摆在桌面上,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料,如十三等,能否从寻常材料中发现不同寻常的问题。发明、发现,孰是孰非,今天执着去谈已没什么意义,因为学术研究的要义,贵在发现的同时,也必须贵在发明。这次会议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大都属于这类问题。尽管方法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辨伪存真的精神。当然,学术水准的提高,还不仅仅需要积累,更需要学术的见识。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说,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的境地。如果只有文献史料的积累整理而无学术见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专门名家,依然无益。这道理无人不晓,但是很难做到精致。原因在哪里?《朱子语类·读书法》认为问题的症结,就是缺乏对经典的敬畏,缺乏平心静气的心态。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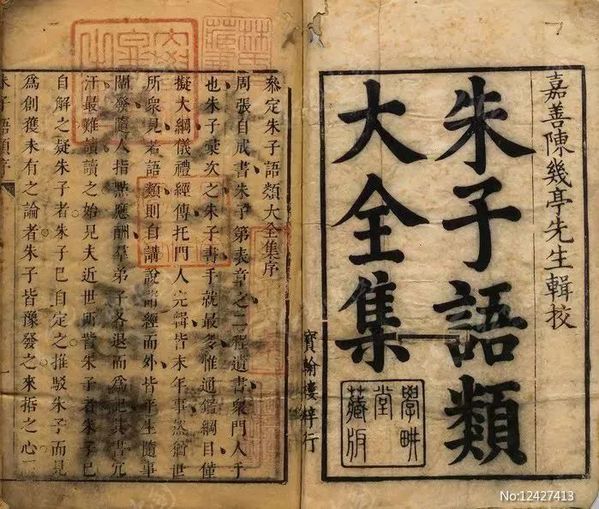
第三,关于文献史料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对史料的重视不够,留下教训。而今,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有古典文献研究工作者认为,只有文献史料才是学问,有些研究为史料而史料,为考证而考证,其实并没有多少学术意义,更没有学术史意义。这是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事文献史料研究的学者,多埋首故纸堆,自拉自唱,自我欣赏。我们这些从事文献史料研究的学者,是否可以考虑为社会、为大众做一点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把我们的研究与社会的需要稍有结合呢?文学研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假史料泛滥,或者仅仅依据微不足道的细节否定整体,以偏概全。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学术的专精研究,二是学术的普及工作。专精研究,是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学术的普及工作则未必得到所有学者的重视。从历史上看,第一流的文献史料研究工作者,他们心中总是装着大众读者,郑玄遍注经典,清人整理文献,很多就是从普及着眼的。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普及的难度,不亚于精深的专业研究。我倡议,文献研究工作者,还是应当做更加有用的学问,这种学问,既为学术界提供有用的文献资料,也为社会为大众提供有用的知识。而后者现在尤其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第四,对中华文学史料的再认识。沙畹《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说:“中国并不总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无需追溯到上古时期,从公元三世纪初到七世纪初以及从十世纪初到十三世纪中,中国分裂为两个或多个敌对的王国。中国之所以在内战之后总能走向统一,并不是出于地理原因:北方省份和南方省份之间差异极大,而且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大河高山,它们充当了不同国家的天然界限。如果说国家最终还是统一了,这难道不应该从文化和心理亲和力方面找原因吗?其中,文学是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一个高倍放大器。”[3]从这个放大镜里,我们注意到,中华文学史料范围很宽,还有很多扩展的空间,譬如我们的多民族文学史料问题,现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我到新疆喀什,拜谒了立于城头的班超雕塑。那里还有一座清真寺,十二世纪在那里产生了一部著名的维吾尔族的书。我把这两个连起来得到一个感觉,汉帝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统领西域三十六国,从汉武帝到今天一天没有放弃,一寸土地都不能丢。在广西合浦,我看到了东汉出土的文物,包括很多精致的项链和民间器物。这些东西可能是因为公元七十九年火山爆发被掩埋。广州有个南王墓,那里出土了很多汉文帝时期的精致银器和金器,这些东西是属于边疆地区,但它们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都有反映。
中华民族不论地域多么辽阔,民族多么不同,但是他有一个共同的向心力,就是文明的向心力。中华文学的表现形式多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二〇二一年十一月,我在参加民族文学史料分会年会的时候,做了一个发言,强调了民族文学史料研究的五难。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比如说各个地区的宗教观念不同,家国观念不同,最后殊途同归,汇集而成中华文学的滔滔江河。在探寻中华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批评标准,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
中华文学博大精深,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这需要我们来清理挖掘。现在学科划分比较糟糕,学科划分,原本是一个进步,但是走到极致就是退步。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的优势,跟我们整个思维一样,就是强调整体性。而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其弊端也就越来越明显。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苏东坡有一句诗,“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意思是写诗太实,就不是好的诗人。好诗是易懂难解,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佛教徒讲看山是看山,看水是水,修道几年之后再看,感受就不一样。我主张不仅要有学科意识,更要有问题意识,碰到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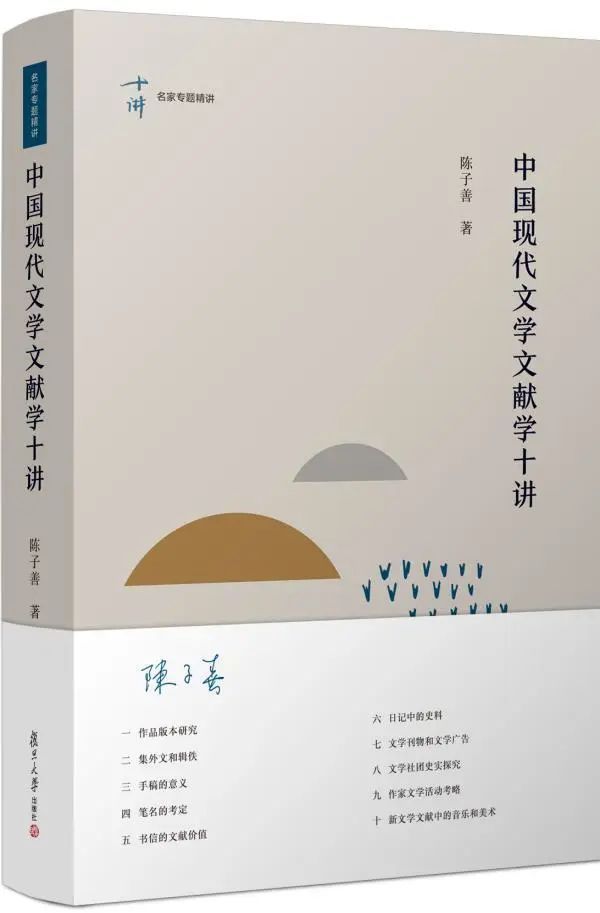
第五,注重文献史料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结合。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推动学科的进步。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整体性的思考,回到历史现场,对当时文学作宏观的考察。
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中华文学史料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得起岁月的检验,很多结论、很多材料,多少年后还时常为后来者提及。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学术同仁齐心协力的结果,也与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能有机会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真要感谢三十多年前创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前辈学者。他们为学会的定名极有前瞻性,不叫中国文学史料,而是中华文学史料,在今天,多么切合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抚今追昔,我们在感动之余,更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应该传承前辈精神的那份文化责任。
本文原刊于《人文》集刊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一九二八年。
[2]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云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第6页。
[3] 沙畹:《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收在《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二〇一四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