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灾害诗歌研究”阶段性成果(19FZWB085)。
内容提要:唐诗中的灾害书写颇为丰富,李白也不乏涉灾之作,《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为其灾害诗的代表作,能充分体现李白灾害文学的书写特色。在对自然灾害的文学表现中,李白往往采取虚实结合的手法,融灾害写实于政治寄托之中。在强烈的个人情感背后,凝聚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丰富了灾害书写的文学内涵。这既是对先秦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对魏晋六朝以来灾害诗歌创作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对自然灾害的诗化表现及其寄寓的文人批评,是灾害文学的最重要特征,李白有关“苦雨”的文学书写,是写实性与抒情性的有机融合,也是李白灾害诗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李白 灾害诗 “苦雨” 写实精神
灾害的发生对人类社会生活往往影响巨大,文学对于灾害的表现也从未缺席,灾害文学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作为唐代社会历史的诗化补充,唐诗中的灾害书写也颇为丰富,不仅涉及范围广、形式内容多,且李、杜等大家也概莫能外,并各具特色。在李白的创作中,也有直接或间接涉及自然灾害的写实文学,其对“苦雨”的灾害书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重视。
一、“苦雨思白日”:从自然“苦雨”到心中“苦雨”
由于目前学界对于灾害文学概念尚无明确的界定,本文所言李白的灾害诗均取其广义,即只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灾害的诗作,均视为灾害诗,既包括直接表现灾害的诗歌,也包含涉及灾害或灾害意象的诗歌。其中有涉及水灾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和《公无渡河》,有涉及旱灾的《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有涉及冰雪寒冻之灾的《北风行》和《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有涉及饥歉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还有可能涉及风灾的《新林浦阻风寄友人》,以及表现天灾人祸交织背景下的民生疾苦的《北上行》等等。

总体而言,李白间接涉及灾害之作较多,有的虽未直接描写灾害,但也有对灾情的间接表现。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1]有学者认为此诗表现安史乱后江淮之饥歉[2]:田家以“雕胡”野米待客之情景,诗人眼见田家之饥苦,又感于“漂母”之朴善,以致“三谢不能餐”。有的诗歌甚至只涉灾害意象,比如《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中的“龙怪潜溟波,候时救炎旱”[3],就是用了“龙怪救炎旱”的灾害思想观念以及潜龙伺用的隐喻表达。有些诗歌表现灾害则较为直接,如《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炎赫五月中,朱曦烁河堤。……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君王减玉膳,早起思鸣鸡。漕引救关辅,疲人免涂泥。宰相作霖雨,农夫得耕犁。……”[4]这首诗明显涉及秦地一次旱灾。据《旧唐书》所载,天宝六载(747)“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台寺、府县录系囚,死罪决杖配流,徒已下特免。庚寅始雨”;天宝九载(750)“三月……时久旱,制停封西岳。夏五月庚寅,以旱,录囚徒”[5]。据此可断,李白诗很可能表现了天宝年间的一次抗旱救灾活动,同时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灾害思想及灾害应对措施。
唐人普遍继承了汉儒的灾害思想,主要秉持以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为基础的灾害天谴观,认为“灾变应天,实系人事”[6],政道有失,则阴阳失序,天降灾害以“谴告人君”,使之“觉悟其行”“悔过修德”[7]。灾害发生后,唐朝统治者通常会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祈禳弭灾。《唐六典》即云:“凡京师孟夏已后旱则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皆于北郊望祭;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修雩。……若霖雨,则京城禜[8]诸门……”[9]除祭祀禳灾外,唐统治者一般还会采取求言罪己、虑囚简刑、避正殿、减膳食以及蠲免赈济等多种措施进行修德理政,以答天谴。李白《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即表现了天降大旱后,唐朝统治者采取伐鼓祈雨、减膳修德、漕引抗旱、输粮救饥等灾害应对措施。
如果说《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还属间接表现灾害的话,那么《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以下简称“苦雨”诗)则更为直接地描写了一次雨水之灾,可谓李白灾害诗的代表作。诗曰:
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其一)
苦雨思白日,浮云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阴阳乃骄蹇。秋霖剧倒井,昏雾横绝 。欲往咫尺途,遂成山川限。潨潨奔溜闻,浩浩惊波转。泥沙塞中途,牛马不可辨。饥从漂母食,闲缀羽陵简。园家逢秋蔬,藜藿不满眼。蟏蛸结思幽,蟋蟀伤褊浅。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绿藓。投箸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其二)(《李太白全集》卷九,第2册,第563—565页)
关于“苦雨”,《初学记》云:“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三日已上曰霖,久雨为霪。”[10]《礼记·月令》:“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郑玄注:“时物得雨伤。”[11]可知“苦雨”又有伤物之害。《左传·昭公四年》:“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臧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东汉服虔解“苦雨”:“害物之雨,民所苦。”[12]可见久雨害物,民为之而苦乃称“苦雨”。
唐代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水灾最为典型,也成为唐诗的重要题材。水灾多由雨水过多所致,唐诗中多见“大雨”“苦雨”“霖雨”“淫雨”“久雨”等水灾书写,而“苦雨”诗尤为多见,如孟浩然《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高适《苦雨寄房四昆季》、杜甫《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白居易《和韩侍郎苦雨》等等。李白《苦雨》可谓唐代“苦雨”诗代表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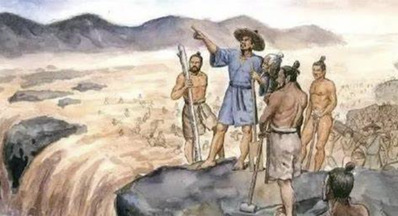
至于本诗写作时间,学界说法不一[13],多认为当作于开元十八年(730)李白首入长安求仕时期[14]。郁贤皓依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开元十八年说”,认为该诗当作于开元十九年[15],但并未就此“苦雨”深入考察,而胥树人、康怀远、王辉斌等学者虽以“苦雨”二字为契机,结合有关史料进行考察,但“苦雨”显然并非唯独此年才会发生,开元十八年的长安也可能有“苦雨”之灾,故兹从十八年说。安旗以为,正是在本年,李白经南阳初入长安,结识张说次子张垍(玄宗女婿、玉真公主侄婿,时拜驸马都尉),但张垍只将李白诱至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中暂住,并未为其仕途奔走,使初入长安的李白被迫蛰居公主别馆,而时值霖雨路断,前途未卜,遂借山中苦雨抒写受冷遇之情[16]。此说可信。唐代雨水之灾以秋季为甚,秋霖苦雨在唐诗中也颇为多见,而李白将这次雨水之灾写得更是有声有色,既写出了雨水之灾害场景,也表现了雨水灾害对诗人生活及精神状态的严重影响。
第一首先写秋霖之灾,进而抒苦雨之情,其中“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二句融情于景,由天色写到人情,为诗人“苦雨”之情张目。“昏垫”有“迷惘”之意,常指水灾,如《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孔颖达疏:“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无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灾也。”[17]又张铣注谢灵运《游南亭》“久痗昏垫苦”曰:“痗,病也,昏雾垫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18]言霖雨之苦使人精神抑郁昏惑,似处于病中。因此,李白亦以“昏垫”言其精神抑郁昏惑,似沉溺而困于水灾,备受霖雨之苦,从而表现了“李白因苦雨而怨天,而尤人,而烦恼”[19]之旨。
第二首进一步描写“苦雨”情景,且将现实人事与自然灾害相结合,抒写怀才不遇之幽情。开头四句似有现实批判意味。“苦雨思白日,浮云何由卷”二句暗含“浮云蔽白日”之典故。《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云:“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李善注:“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陆贾《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20]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追忆其遭谗被逐出京,亦云:“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可见其《苦雨》诗用浮云蔽日之典不无深意:欲彰其才,成就功业,然干谒未果,遭人冷落,何时云开日出,见用于明主!此处不仅影射邪臣蔽主,致使兰艾不辨,英才未显,发其不遇之幽愤,亦伤“谁贵经纶才”之世道。诗末“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二句,更可见李白用“浮云蔽白日”之典喻怀才不遇之深意。同时诗人以“欲往咫尺途,遂成山川限”之灾情,暗喻其与人主虽只咫尺之途,却有山川之隔,写其遭受冷遇而被迫蛰居此地的无奈与愁苦,并借大雨滂沱、泥沙塞途、牛马不辨的灾情描写,尽情宣泄其欲济无梁,渴望遇合而不得的苦闷心情。
李白可谓书写了两种“苦雨”:一是诗人眼前所见自然环境中的真实“苦雨”;二是作者因备受政治冷遇而产生的心中之“苦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个人政治前途之失望,这是令作者最为苦恼的“苦雨”。至此,作者笔锋再转,进一步写到整个时代政治环境之“苦雨”。此笔锋之转变,实际上完成了诗歌从灾害描写向社会批评的转换。对个人命运、社会弊端的苦闷、愤懑,与苦雨的难堪、压抑混合在一起,种种情绪涌上心头,从而使李白此时变成一个社会批评家。这也使其灾害书写实现了最大的社会价值。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虽被誉为盛世,但其实这个所谓的“盛世”也有着灰暗阴冷的一面,愁苦之音亦多出于盛唐诗人的笔下,文人政治理想的普遍落空,使其多发盛世之悲鸣[21]。李白《苦雨》诗中“稷卨和天人,阴阳乃骄蹇”二句即隐含着作者对于时任宰相的讽刺与批判,其实就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给文人所带来的上升渠道不畅表达不满。稷、契为舜之贤臣,此指宰相。《旧唐书·五行志》载:“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闭坊市北门,驾车者苦甚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致兹恒雨,令我污行。’”[22]自汉以来,古人普遍认为宰相有“燮理阴阳”[23]之责,其“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24],若阴阳不和而致灾,宰相便难辞其咎。因此,李白借天人感应思想,既直接表达了对宰相造成的“政治苦雨”的不满,也间接表达了对于当时整个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政治或社会苦雨”的不满,由此突显出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要之,李白《苦雨》二首既描写了霖雨灾害场景,又借长安雨水之灾浇其胸中块垒,暗讽时相不能任人唯贤,从而批判社会之不公,发士子不遇之幽愤,将现实灾害场景中的“苦雨”与心中之“苦雨”,以及作者所处时代政治环境之“苦雨”联系起来,将诗歌境界上升到对整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的高度,大大丰富了灾害书写的文学内涵。而前述《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中“宰相作霖雨”一句,看似用典[25],实际也将天旱与宰相之责关联起来,亦有类似于《苦雨》一诗的政治批判意味。这种批判性,正体现出李白灾害文学书写的深刻思想性,也使李白的灾害作品更具研究价值。
二、继承与超越:李白“苦雨”诗的灾害文学渊源
灾害文学书写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灾害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展示,成为后世灾难文学的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26]。李白以“苦雨”诗为代表的灾害文学书写,不管是以想象为基础的灾害场景的虚拟,还是以现实灾害情景为对象的实写,实际上都体现出对于现实的严重关切,于浪漫情思的抒写中不乏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这种艺术表现继承与发扬了先秦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精神和艺术风范,并对汉魏六朝灾害文学书写有所继承与超越。通过考察李白灾害诗歌代表作,可进一步探讨此类诗歌的文学传统,以及在灾害文学书写上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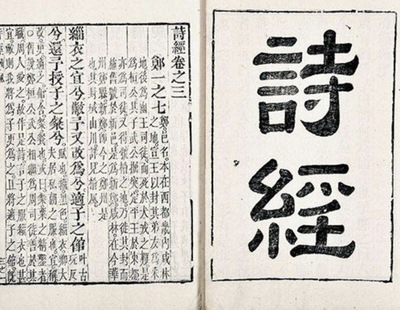
有关雨水灾害的文学书写在古代灾害文学中最具代表性,因水灾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往往由降水所致,自远古洪水神话以来,水灾的文学书写便非常丰富。先秦时期除了神话和散文外,《诗经》中的《召南·江有汜》《小雅·正月》等也涉及雨水之灾。到了汉代,已有较为完整的水灾诗,其中表现黄河水患的汉武帝《瓠子歌二首》较为引人注目[27],而另有一首表现雨水之灾的《风雨诗》则尚未引起关注:“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见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槙到忘相加,天门狭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诗教海兮诚难过。”[28]展示了一幅风雨交加、雨水成灾的灾害场景。可以说,灾害文学史上直接描写雨水灾害的诗歌当自此诗开始,为后世“苦雨”诗之滥觞。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瑀、傅玄、张协、鲍照、江淹等多位诗人先后书写“苦雨”;唐代除李白外,孟浩然、杜甫、高适、元稹、白居易等不少诗人均写有“苦雨”诗。此后,“苦雨”不仅是历代诗人笔下的重要题材,而且通过与前人“苦雨”题材诗歌相比较,不难发现,李白《苦雨》明显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六朝的文学传统。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直接引用魏晋诗歌语汇,或化用魏晋诗歌意境。“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作“苦雨”诗云:“苦雨滋玄冬,引日弥且长。丹墀自歼殪,深树犹沾裳。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伤。登台望江沔,阳侯沛洋洋。”[29]诗歌描写玄冬苦雨情景,并抒发其抑郁感伤之客情,景与情合,情由景生,已是一首较为成熟的“苦雨”诗了。而李白《苦雨》不但同样写出客行之感伤,而且开篇也与阮瑀“苦雨滋玄冬”之发端相类。此后晋代傅玄《雨诗》曰:
徂暑未一旬,重阳翳朝霞。厥初月离毕,积日遂滂沱。屯云结不解,长溜周四阿。霖雨如倒井,黄潦起洪波。湍流激墙隅,门庭若决河。炊爨不复举,灶中生蛙虾。(《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上册,第571页)
傅玄诗中书写了滂沱大雨,积雨成“洪波”,“湍流”冲墙角,门庭若江河决堤,灶中炊事不举而蛙虾出没的灾害场景。此诗对李白《苦雨》的影响也极为明显。李白不仅直接化用傅诗“霖雨如倒井”“炊爨不复举”等句(李诗为“秋霖剧倒井”“厨灶无青烟”),诗中所描写的雨水灾害情景也与傅诗颇为相似,李诗中的“刀机生绿藓”与傅诗中的“灶中生蛙虾”,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除了化用语典与意境,风格与写法上也深受魏晋诗歌的影响。傅玄《雨诗》明显可见其灾害写实性,其子傅咸的《雨诗》也主写客观之灾情[30],而其后张协则在灾害写实基础上更多融入主观情感之寄托。张协《杂诗》其十:
墨蜧跃重渊,商羊儛野庭。飞帘应南箕,丰隆迎号屏。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霖沥过二旬,散漫亚九龄。阶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割,人怀昏垫情。沉液漱陈根,绿叶腐秋茎。里无曲突烟,路无行轮声。环堵自颓毁,垣闾不隐形。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君子守固穷,在约不爽贞。虽荣田方赠,惭为沟壑名。取志于陵子,比足黔娄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上册,第747页)
张协诗被锺嵘《诗品》列为上品,这首诗歌更被赞为“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与曹植《赠白马王彪》、王粲《七哀》、阮籍《咏怀》、左思《咏史》等名篇并称[31]。不同于西晋太康模拟之风,张协诗“挥洒匠心,纵横尽情”[32],将写实与寄托相结合,表现出对汉魏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复归[33]。
此诗不仅极写雨水之大,雨势之急,历时之久,灾情之重,影响之剧,将灾害造成的荒凉、萧瑟的破败景象写得生动逼真,而且借此抒写了久雨后抑郁孤清的“昏垫”之情。“洪潦浩方割,人怀昏垫情”也成为后世“苦雨”诗的抒写范式,对李白《苦雨》当有重要影响。首先,李白对秦中雨水灾害情景的描写,便有“景阳苦雨”脱胎之嫌,如其“泥沙塞中途,牛马不可辨”之句与张协诗“路无行轮声”之意相近;其“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绿藓”与张协“里无曲突烟”“堂上水衣生”,“投箸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与张协“红粒贵瑶琼”等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李白和张协一样“将写实与寄托结合”,将灾害写实与其不遇之感结合起来,“挥洒匠心,纵横尽情”,只是与张协的“君子固穷”所不同的是,李白于怀才不遇、功业未就的郁愤不平中,更多一份“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自信豪迈之气。最后,李白《苦雨》诗其二在诗歌写法与整体风格上,皆与张协此诗极为相近。二者均通过对雨水灾害场景的生动描摹,渲染一种凄清孤寂的情感氛围,感发出孤独悲凉的情绪,借此表现诗人在灾害情景中的精神状态,抒写作者内心的坎壈情怀。
第三,受因物感兴、借景抒情传统写法的深刻影响。先秦以来,灾害诗歌创作虽有明显的写实倾向,但却朝着灾害写实与情感写虚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诗经》中《小雅·正月》所云“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即以雨水灾害渲染烘托抒情氛围,有人以为其“以阴雨行车比乱世弃贤”[34],这里的雨水灾害成为比兴媒介。故在“苦雨”诗创作中,诗人往往既描写淫雨成灾的自然景象,又抒写由灾害所触发的愁苦情绪,雨水灾害便主要成为诗歌抒情言志的背景和媒介。例如,南朝鲍照的《苦雨诗》:
连阴积浇灌,滂沱下霖乱。沉云日夕昏,骤雨望朝旦。蹊泞走兽稀,林寒鸟飞晏。密雾冥下溪,聚云屯高岸。野雀无所依,群鸡聚空馆。川梁日已广,怀人邈渺漫。徒酌相思酒,空急促明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九,中册,第1306页)
表现了在“连阴积浇灌,滂沱下霖乱”的灾害天气里,鸟禽晏飞,走兽见稀,野雀无依,川梁日广,而怀人相思的凄凉情景。江淹《张黄门协苦雨》亦于“愁霖贯秋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第1574页)的文学表现中抒写了秋霖中离群索居的冷寂与孤独,以及岁暮萧瑟的愁绪与感伤,体现了灾害心理与悲秋情绪的自然交集。两者虽然都实写了雨水灾害场景,但更突出表现了灾害天气中的情感意绪,可见诗人的灾害心理与物候变化之间有着密切关联。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认为:“物候在诗人的生命意识的萌芽过程中,起了一种‘触媒’即催化剂的作用。”[35]自然灾害中物候的异常变化更会激烈地刺激着诗人的敏感神经,激发起强烈的生命意识,触发诗人的诗兴,使他们于灾害场景的描述中融入并宣泄其情感意绪,故春季雨浓风骤惹人伤春,秋来苦雨萧萧易致悲秋。而在伤春和悲秋这中国古代两大诗歌生命主题的表达中,又常常离不开雨水这个“触媒”,所以雨水灾害诗歌中的悲情氛围较为浓厚,实与灾害天气对诗人情感心理的影响不无关联。阴雨天气不仅容易使人产生抑郁情绪,雨水灾害的发生还往往会引起诗人的生命苦难意识以及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故张协因“洪潦浩方割”而怀“昏垫”之情,何况游子他乡,前途茫茫!阮瑀亦因玄冬苦雨而生“客行”之感伤。刘勰所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6],即与此合。因而在诸多书写雨水灾害的诗歌中,作者更多是借以抒发种种感伤情绪,往往以“雨(水)”中之窘促、路途之阻难,寄托其“不遇”之心事。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即云“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37],以三川大水致道路阻滞难行之灾情,发其欲济无梁的士子失路之慨叹。李白《苦雨》也以“欲往咫尺途,遂成山川限”表达出类似的意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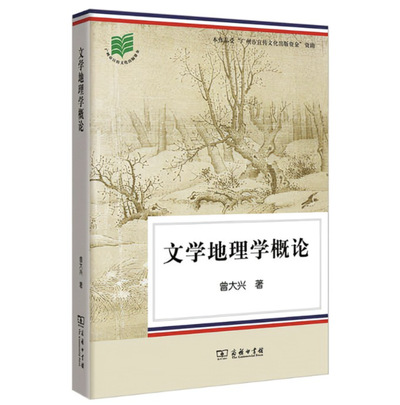
自然灾害是情感发抒的“触媒”,李白《苦雨》对开元年间这次雨水灾害场景进行了真实描写,其渴望遇合而不得的苦闷心情也在灾害情景的描写中得以发抒,自谓满腹“经纶”却无人知遇,干谒权贵却遭冷遇,独酌自宽却又无法抑制内心的忧愤。其借“翳翳”秋霖抒“无鱼”之怨时,不仅化用傅玄、张协“苦雨”诗语典,而且沿用了前人“苦雨”诗创作的基本范式,创造性地将灾害场景描写与对不遇之情的抒写巧妙结合,于客观灾害写实中蕴含主观情感之宣泄,明显继承与发展了六朝以来的书写传统。
李白的灾害书写与前人又有明显不同,其灾害表现更具思想高度。就雨水灾害书写而言,前人多以“苦雨”为抒情媒介,李白则由写实而至抒情与批判,以“苦雨”灾害进行现实讽喻,将矛头直指封建上层统治者,更具现实批判精神———通过书写雨水之灾,对造成“阴阳骄蹇”的时任宰相进行讽刺,对统治者不能任人唯贤进行批判,对因“浮云蔽白日”而致士子不遇的不公平社会现象进行深刻揭示。
要之,李白的灾害书写充分体现出浪漫诗风中的写实精神,不仅继承了先秦以来灾害文学书写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是继承与超越了魏晋六朝以来灾害诗歌的文学传统与艺术精神,往往将自然灾害与个人遭际及政治现实相联系,体现出高超的写实艺术和一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未完待续)。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24年第03期
作者简介:龙珍华,博士,教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灾害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fayqqv3WFftQ2i6rUrSs7Dqu5gQImZ1Tbs5ttZ-Un8MA3PsVGVGXBc_IbjC-qJt4bzxR5vF8ycN0Ims4Eq76UShmKwNnEeFMT0ZJqJYqmoZqcDsRuf49w5XnJ1qKskfcZhOJrxvXMUCCUAoW-xa_fywYiTr8NILHt2T05a-zT8=&uniplatform=NZKPT
参考文献:
[1]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册,第1195页。
[2]参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13页;李白撰,安旗等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一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册,第1189—1190页。
[3]《李太白全集》卷一四,第3册,第802页。
[4]《李太白全集》卷一八,第3册,第1015—1016页。
[5]《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第1册,第221、224页。
[6]《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4册,第1354页。
[7]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四《灾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8]“禜”是一种为禳除灾害而祭祀神灵的行为。
[9]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4页。
[10]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23页。
[11]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礼记集解》卷一六《月令第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上册,第447页。
[12]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春秋左传诂》卷一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册,第659页。
[13]参见王辉斌《李白〈苦雨〉诗的再考订———兼论三入长安说者的依据问题》,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李白研
究》(1992—1993年集)1992年9月版。
[14]参见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1页。
[15]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卷七,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册,第1079页。
[16][19]安旗《我读李白〈苦雨〉诗》,《人文杂志》1998年第5期。
[17]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163页。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二《(诗)游览》,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册,第409页。
[18]《六臣注文选》卷二九,中册,第538页。
[20]《李太白全集》卷一九,第3册,第1057页。
[21]杜晓勤《从“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鸣———开天诗坛的另一考察维度》,《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22]《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4册,第1363页。
[23]陆曾禹原撰,倪国琏检择,蒋溥等删润《钦定康济录》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3册,第283页。
[24]汉左相陈平对汉文帝所云宰相之职(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〇《张陈王周传》,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7册,第2049页)。
[25]《李太白全集》卷一八,第3册,第1015、1017页。
[26]王秀臣《灾难视野中的文学回响———先秦灾难的文学表现及其意义》,《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93—94页。
[2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二,上册,第328—329页。
[2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三,上册,第381页。
[3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上册,第609页。
[31]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347页。
[32]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353页。
[33]宋展云《论张协与两晋之际文学新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34]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卷一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1页。
[35]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8页。
[3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〇《物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册,第693页。
[37]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308页。